【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有一次贝多芬和歌德走在一起,遇德国皇帝的队伍经过,歌德在路旁脱帽致敬,贝多芬大踏步直穿车队而过。这一细节的真实性我总有点怀疑,那时的皇家“保卫”就那么松懈?不过他蔑视皇帝是真的。所以第三交响乐(英雄)原要献给拿破仑,见拿破仑称帝,就立即收回。他对歌德的举动颇为不屑。人们多赞赏贝多芬的骨气。这使我联想起《世说新语》中管宁与华歆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不过关于管宁与华歆的为人和全面经历,史书还另有说法,此处不论。
不过人是复杂的,贝多芬也有另一面,也曾为政治服务,唱颂歌,而且决不是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小动作。

(图片源于网络)
和许多艺术家一样,贝多芬的一生苦多于乐,生活的磨难、本人的特异个性、社会的不理解,使其大部分时间怀才不遇,生活潦倒,更不用说完全失聪的痛苦了。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只不过他也曾有过短暂的风光,作品能使当时顶级演奏家集体参加演出,奥地利全民都是他的“粉丝”,当时的王公贵族都为之折腰。这也是他收入最高,几乎是唯一不为债务缠绕的时期。这好运是怎么来的呢?
1813年,已经43岁的贝多芬刚刚失恋,事业、感情都处于低谷,加上身体的病痛,精神接近崩溃,几乎丧失创作能力。此时刚好是拿破仑在俄罗斯全军覆没之后在意大利、德国又节节败退,拿破仑称霸欧洲的日子已接近尾声。这一形势大大鼓舞了一向为法国所欺压、饱受屈辱的奥地利人。一时之间民族情绪高涨,拿破仑一连串的败绩就是他们持续不断的狂欢节。此时贝多芬的一位好友建议他写一首乐曲庆祝威灵顿公爵在意大利打败拿破仑的弟弟之役。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威灵顿的胜利》,在维也纳两场慰劳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伤兵的音乐会上演出,获得轰动反响。我无缘听到这一乐曲,据某些资料称自始至终非常高昂,甚至有以乐器模拟枪、炮之声。从此贝多芬一举成为奥地利家喻户晓、最受爱戴的音乐家。接着, 他循着这个路子又创作了《日耳曼人》交响乐以庆祝巴黎沦陷于普鲁士军队;《致幸福国家的奠基人》和《光荣时刻》两首大合唱献给维也纳代表大会,后面一首大合唱的乐章中甚至一反其蔑视王侯的傲气,包含有赞颂俄国沙皇以及普鲁士、丹麦、挪威、奥地利等国的君主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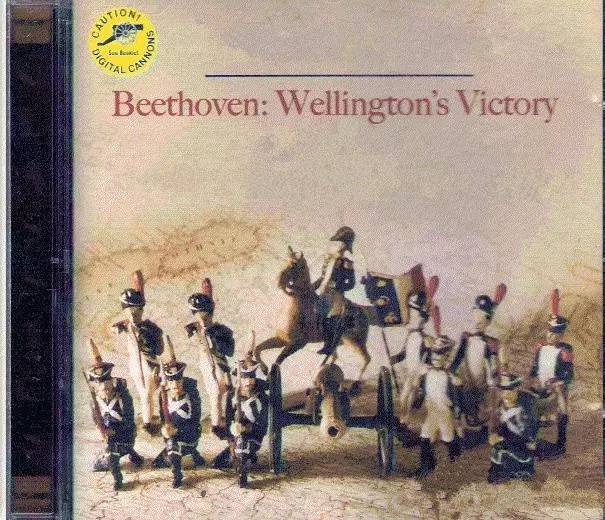
(图片源于网络)
1814年的贝多芬可谓多产,演出也很频繁,名利双收。但是这些作品恰恰是他的败笔,后人称其浅陋、煽情一如庸俗的流行歌曲。他的传世之作第七交响乐却作为《威灵顿的胜利》的附属品演出;而第八交响乐也是乘着这股风才得以首演。今天人们大概很少有人听说过那几首为政治服务的乐曲。实际上,热闹一阵之后,乐评界对那几首曲子立即恶评如潮。有深厚修养的奥地利音乐界还是有足够的鉴赏力的。可以说,这一年,贝多芬以浪费他的天才,放弃了清高自守为代价,用一系列迎俗之作,换来了一时的名利。讵料“粉丝”无情,热潮迅速退去,贝多芬的命运又急转直下,陷入深谷达数年之久。然而天才终究是天才,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创作成就了天鹅的绝唱,也幸亏那些劣等品已经淹没无闻,除少数专业史家予以钩沉外,不会再现身,连累乐圣的盛誉。
这就有一个问题,是否真艺术一定在苦难中产生?“文章憎命达”是否普遍规律?这倒未必。大艺术家(广义,包括音乐家、诗人)生前就享受尊荣,生活优裕的也不乏其人。只是不世出的天才往往有异于常人之处,因而不容易为当代人所理解,要忠于自己,就要耐得住寂寞。穷、达要看客观环境和机遇。有一点是肯定的,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应景、迎俗、奉命之作往往不是出自艺术家的内心,而是主题先行,一开始就迎合某种需要,其美学价值就要打折扣。所以中国古代大诗人或有御前奉诏之作,大都不在其传世的佳作之列。当然也有例外,临时想到的是李白的三首《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完全是奉诏之作,而且是歌颂杨贵妃的,“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够肉麻的了,成诗的背景颇为不堪。但是就辞藻本身而言,却也有其独特的魅力,这是李白才气过人之处,只能算特例。不过如果李白大部分作品多是这一类的,无论如何成不了伟大的“诗仙”的。
古人只是个人迫于生计,偶一为之,至于今之某大导演,前期颇有佳作,表现了不俗的才华和一定理念和良知。我曾一度期望他成为当代电影界的大师。然而不久,与超常的权力和财富相结合,“华丽转身”(还转得回来吗?),凭借旁人所没有的特权,屡屡挥霍民脂民膏,任意调动和滥用无数专业和群众演员,以破坏自然景观和扭曲一代中国人的审美观为代价,成就其所谓“辉煌”,留下的烙印,岂止是个人的败笔而已!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