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坏事推给别人,推给一个替罪羊,好像自己永远无辜的人,难免不重蹈覆辙
有人说,中国小说家是讲故事人,而法国小说家都是哲学家。此话有点道理。中国人喜欢外在的情节远胜于对人复杂内心的挖掘和揭示。所以,武侠小说家可以堂堂正正在文学家排行榜上稳坐前几把交椅,而总也有教授之类的精英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当之无愧。可也因为如此,在中国小说家中几乎没有福楼拜和普鲁斯特这样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卡拉马卓夫兄弟》或《魔山》这样的小说。
讲故事人,只要故事生动曲折,引入入胜就行了。哲学家式的小说家则不是为了让人消遣,而是为了让人在小说这种虚构中看到世界人生更深切的东西,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自己。讲故事的小说是看过就算,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它只要向外铺陈;而哲学家-小说家的小说则是向内开拓,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纯粹也更复杂的世界和自我,往往令读者沉吟低徊,不能自已。
当然,这个世界上喜欢看《鹿鼎记》的人一定远过于喜欢读《复活》的人。可艺术的价值或精神的内涵不是可以量化的。其实,说哲学可能有点玄,向外的艺术和向内的艺术之优劣高下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中国式离婚》的制造者,显然深谙中国人喜欢外在情节的审美倾向,因此,凡是夫妻关系中可能想到的佐料,如无端吃醋、第三者、性无能等等,都用上了。《克莱默夫妇》也是讲一个离婚的故事,却没有那么多花里胡梢的佐料。它只是从人心深处描写离婚给家庭三个成员——丈夫、妻子和孩子带来的情感冲突和困境。因为触及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的现代人的存在状态,虽无外在的所谓戏剧冲突,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当然,《中国式离婚》是纯商业制作,《克莱默夫妇》是所谓的文艺片,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的文艺家和读者一般喜欢外在的东西而很少向内下功夫,却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其实,注重向外而不爱向内,远不只是我们的审美倾向,更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这是现代性给我们心灵气质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古人从孔夫子开始,就强调反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等等。理学家更是知道人是受心灵支配的,心正行自正,心不正则一切都不堪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根本的也是自己。外在问题的根子在内部,在心。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要有担当,而不能把它归于种种外部因素。吴伟业不得已仕清,他不把责任推给外在因素,而是愧悔终身:“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悲怆诚挚,字字出自肺腑。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心”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的地位日益下降,而外部因素意义上的“物”则成了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直指本心的传统变成了外部因素决定论。从此,我们的眼睛总是往外看,而不再往内看。我们相信制度决定一切,而忘了制度取决于人(康德说过,一群强盗也可以成立一个共和国)。我们总是要让不在场的人和事为在场的人负责,比如,让古人和传统为近代的一切不幸负责;用上当受骗来解释自己的积极参与;把一切推给一个罪魁祸首,等等。浩劫过后,一听要自我反省,有人就勃然大怒。除了公认的几个人,大家都是好人,都是受害者,无论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而受害者总是令人同情的,要是受害者还能呼吁讲真话或反省未能做到“修辞立其诚”,立刻能让人感动莫名。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做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是个犹太人,二战期间被德军俘虏并被送去当苦力,他在巴黎的妻女东躲西藏,在东欧的父母兄弟被纳粹合作者杀害。这位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家却提出:受害者也要部分地为自己的受迫害负责,纳粹的土壤存在于“民众”之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因妻子是犹太人而在恐怖中捱过纳粹统治时期,可战后他马上反省德国人的罪责。深受极权统治之害的哈维尔得出结论:“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驱逐出去。……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付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因为人家有宗教背景,因而有忏悔的传统和意识。这实在是小看了人家。那么自觉地提出责任问题,实在是因为,能否为自己、进而为天下的事情承担责任,是公民和臣民根本区别之所在。■

张汝伦:向内,向外?
2007年03月19日 10:47
版面编辑:运维组
- 推广
图片推荐
编辑推荐
- 能源 | 【特稿】为何换表后费用大涨?
- 金融 | 范一飞案一审开庭 受贿3.86亿元
- 科技 | 华为P70系列如何搅动市场?
- 财新周刊 | 黄金因何暴涨
- 封面报道 | ①阿里退守 ②大厂在收缩
最新文章
- 18:17村镇银行改革化险持续推进 多家村镇银行...
- 17:02打通束缚“科技型国企”新质生产力发展 ...
- 15:08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期盼对中国公民的免...
- 12:34一波数折 吉林四平特等劳模郑小东案再审开庭
- 11:56极氪CEO称将聚焦纯电 没有增程式车型计划
- 08:38中证监发布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 E...
- 08:34中核钛白“定增+融券”套利违规 中信、...
- 08:30被立案调查半年 高瓴QFII基金拟购回...
- 08:27人事观察|宣传系统高官密集调整 常斌转...
- 08:23人事观察|信息支援部队成立 毕毅李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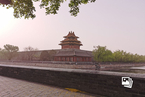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